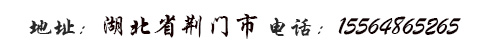名老中医麻黄用药心得1
|
张锡纯经验麻黄解 张锡纯(年-年),字寿甫,籍山东诸城,河北省盐山县人,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。年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,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。著有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。 麻黄,味微苦,性温。为发汗之主药。于全身之脏腑经络,莫不透达,而又以逐发太阳风寒为其主治之大纲。故《神农本草经》谓其主中风伤寒头痛诸证,又谓其主咳逆上气者,以其善搜肺风兼能泻肺定喘也。谓其破癥瘕积聚者,以其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,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,而消坚化瘀之药可偕之以奏效也。且其性善利小便,不但走太阳之经,兼能入太阳之府,更能由太阳而及于少阴(是以伤寒少阴病用之),并能治疮疽白硬,阴毒结而不消。 太阳为周身之外廓,外廓者皮毛也,肺亦主之。风寒袭人,不但入太阳,必兼入手太阴肺经,恒有咳嗽微喘之证。麻黄兼入手太阴为逐寒搜风之要药,是以能发太阳之汗者,不仅麻黄,而《伤寒论》治太阳伤寒无汗,独用麻黄汤者,治足经而兼顾手经也。 凡利小便之药,其中空者多兼能发汗,木通、萹蓄之类是也。发汗之药,其中空者多兼能利小便,麻黄、柴胡之类是也。伤寒太阳经病,恒兼入太阳之腑(膀胱),致留连多日不解,麻黄治在经之邪,而在腑之邪亦兼能治之。盖在经之邪由汗而解,而在腑之邪亦可由小便而解,彼后世用他药以代麻黄者,于此义盖未之审也。 受风水肿之证,《金匮》治以越婢汤,其方以麻黄为主,取其能祛风兼能利小便也。愚平素临证用其方服药后果能得汗,其小便即顿能利下,而肿亦遂消。特是其方因麻黄与石膏并用,石膏之力原足以监制麻黄,恒有服之不得汗者,今变通其方,于服越婢汤之前,先用白糖水送服西药阿司匹林一瓦半,必能出汗,趁其正出汗时,将越婢汤服下,其汗出必益多,小便亦遂通下。 东人三浦博士,用麻黄十瓦,煎成水一百瓦,为一日之量,分三次服下,治慢性肾炎小便不利及肾脏萎缩小便不利,用之有效有不效,以其证之凉热虚实不同,不知用他药佐之以尽麻黄之长也。试观《金匮》水气门越婢汤,麻黄辅以石膏,因其脉浮有热也(脉浮故系有风,实亦有热),麻黄附子汤辅以附子,因其脉沉而寒也。通变化裁,息息与病机相符,是真善用麻黄者矣。 邹润安曰:麻黄之实,中黑外赤,其茎宛似脉络骨节,中央赤外黄白(节上微有白皮)。实者先天,茎者后天。先天者,物之性,其义为由肾及心;后天者,物之用,其义为由心及脾胃。由肾及心,所谓肾主五液,入心为汗也;由心及脾胃,所以分布心阳,外至骨节肌肉皮毛,使其间留滞无不倾囊出也。故栽此物之地,冬不积雪,为其能伸阳气于至阴之中,不为盛寒所遏耳。 古方中有麻黄,皆先将麻黄煮数沸吹去浮沫,然后纳他药,盖以其所浮之沫发性过烈,去之所以使其性归和平也。 麻黄带节发汗之力稍弱,去节则发汗之力较强,今时用者大抵皆不去节,至其根则纯系止汗之品,本是一物,而其根茎之性若是迥殊,非经细心实验,何以知之? 陆九芝谓:麻黄用数分,即可发汗,此以治南方之人则可,非所论于北方也。盖南方气暖,其人肌肤薄弱,汗最易出,故南方有麻黄不过钱之语;北方若至塞外,气候寒冷,其人之肌肤强厚,若更为出外劳碌,不避风霜之人,又当严寒之候,恒用七八钱始能汗者。夫用药之道,贵因时、因地、因人,活泼斟酌以胜病为主,不可拘于成见也。”(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) 陆渊雷经验论麻黄 陆渊雷(~)名彭年,江苏川沙人。民国元年(年)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、小学,于诸子百家、史、地、物理、算学等书无所不读。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江苏省立师范学校、国学专修馆、暨南大学、持志大学、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。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,研究中医各家学说。民国14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,陆渊雷拜恽为师,协助办校。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,深得两名家之教益。 江湖上的医生,与普通社会的心理,认麻黄为温热性的发汗药,轻易不敢尝试。不错,麻黄是温的,是发汗的,但是麻黄的温,须不比附子、干姜,温煞也有限。说个比方,好比适口的温汤,冬天喝了似乎暖,夏天喝了也并不嫌热。麻黄若与石膏一同用,反变成很凉的凉药,仲景书中的“麻杏甘石汤”“越婢汤”便是麻石同用的凉药。这样一来,麻黄性温一层,可以不必顾虑了。若说到发汗,那就有个研究。汗液中的成分,除却水分以外,多半从蛋白质变成,因此之故,倘若这人有荣养不良的证据,知道他身体内缺少蛋白质时,不可发汗,发了汗时,蛋白质分解消耗得更多,荣养液更要不足了,这个弊端,中医叫做“亡津液”。这是一层。还有一层,汗液流到皮肤面上,就蒸发成汽,飞散于空中。当它蒸发的时候,必须吸收身体的体温,因此之故,倘若这人生出体温的官能不健全,或竟体温低落,不及摄氏表37℃的标准体温时,也不可发汗。发了汗时,体温被吸收得更多,来不及补充,体温低落下去,可以使身体上一切机能都跟着停阻起来,这个弊端,中医叫做“亡阳”。亡津液与亡阳两个弊端,不问什么发汗药都要防它,不但是麻黄。可怪那班俗医,见了三四分麻黄,便吓得倒躲不敢用,却喜欢用紫背浮萍,竟用到二三钱,岂知浮萍的发汗比麻黄要厉害十倍。在下亲见一个病人,吃了一钱半浮萍,一身大汗之后,弄得手瘫脚软,将养了七八个月才得复原。偏是这些懵懵懂懂的社会,不敢吃三四分的麻黄,反情愿吃二三钱的浮萍。 麻黄的效用是发汗,发汗的弊端是亡津液与亡阳。倘使这人津液不亏,阳也不虚,那就不怕发汗,换句话说,就不必畏忌麻黄哩。诸君试看劳力的苦工,哪一天不出几身大汗,再看夏天,哪一人不出几身大汗,何尝见他们亡津液与亡阳呢?至于医药上用麻黄,第一个目的,正因为津液太多;第二个目的,正因为体温太高。津液太多或体温太高而吃麻黄,正如饿了吃饭,里急了出恭,有什么害怕? 什么叫津液太多?就是全身或一部分含有蛋白质的液体太多。例如水肿,是全身津液太多。痰饮(本在胃肠,时师以指呼吸器病,今姑从俗)是气管里一部分津液太多。古书上说的水气病/痰饮病,倘使那些水分利于从皮肤中赶出,那就是适用麻黄的标准,就是用麻黄的第一个目的。依张仲景的规矩,为第一目的而用麻黄,多半与石膏同用。上面说的麻杏甘石汤、越婢汤,就是榜样。什么叫体温太高?就是发热罢了。人体的温度,源源不绝地生出来,也源源不绝地从皮肤放散到空气里去。生出与放散,须得一样多少,才能保持三十七度的标准体温,才合于人体的生活条件。倘若生出不加多,放散又减少时,就要发热;放散不减少,生出加多时,也要发热;生出加多,放散又减少时,尤其热得厉害。不管他生出的多不多,只要放散减少时,统得用麻黄发汗退热,这就是用麻黄的第二个目的。依张仲景的规矩,为第二个目的而用麻黄,必须与桂枝同用,麻黄汤、葛根汤、青龙汤就是榜样。 发热的原因,非常之多,怎么知道是放散减少而应当用麻黄呢?那也不难。第一,病人的皮肤干燥无汗;第二,病人自觉头疼怕冷;第三,脉搏浮。这发热、头疼、恶寒(即怕冷)、脉浮,张仲景叫它做“太阳证”。 如今且说无汗一证,知道皮肤紧闭,体温的放散一定减少了,所以用得着麻黄发汗。好好的人,为什么体温的放散会减少起来?那一定另外有一种病毒,在他身上作怪的缘故。不过人身体对于病毒,天生下来就有抵抗、驱逐的本能。抵抗、驱逐的路道很多,做医生的应该考察他用的是哪一条路道,考察定了,用药帮助他,这是医药的一个原则。考察的有太阳证,就知道身体要把病毒从皮肤里赶出去,那就要用发汗解肌药去帮助他了。因此之故,发热无汗的太阳证,就可以而且必须用麻黄、桂枝,这才是一举两得,既放散体温,又驱除病毒哩。不过有汗的太阳证,就不可以用麻黄,因为既是有汗,可见得发热的缘故并不是体温放散减少,用了麻黄恐防要亡津液,若与桂枝同用,尤其恐怕要亡阳了。 若为第一个目的——逐水气——而用麻黄,无汗的当然要用,有汗的也要用。因为水气病有汗,尤其知道身体要把水气从皮肤里赶出,索性用麻黄,帮他赶个罄尽,病自然好了。既是水气,就不怕他亡津液,不与桂枝同用,也不怕他亡阳。所以仲景书中,麻杏甘石汤、越婢汤的证候,皆是汗出的,而且不一定发热的,而且多数属于慢性病,没有太阳证的。 以上说的麻黄标准,皆从发汗说来,但是麻黄的效用,不但发汗,还能治喘息。本来张仲景用麻黄的证候,十之八九有喘的,俗医却不晓得。吉益东洞说“麻黄主治喘咳水气”,真是不错呢。但是喘咳属于虚的,麻黄却是用不得。例如肺痨病及老年痰喘等,皆不可用麻黄,老年痰喘也有实的,在下曾用麻黄治好一人,那就要有辨别虚实的本领,非三言两语说得明白,只得不谈了。却有一桩,据化验的结果,麻黄的有效成分,不过千分之三,多至千分之五,那么,用五分麻黄,实际药力只得二毫五丝,二毫五丝的药,凭他怎样剧烈,凭他怎样重病,总吃不死人吧。湖北地方通常用一二钱,四川用到三五钱,那才要把细些。江浙通常用三四分,还是不敢吃,在下真是莫名其妙了。(陆渊雷整理)(《陆渊雷医书二种》) 章次公经验论麻黄 章次公(~),名成之,号之庵,江苏省镇江丹徒人,医学家。 民国8年(年)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,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,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,学业兼优。 近世畏麻黄不啻猛虎,而尤以上海为甚,问其理由,莫不以麻黄发汗之力太悍,不慎将汗出不止而死。此等谬说,吾人欲剪辟,姑引吉益东洞麻黄辨误以纠正之,其言曰:吾闻之麻黄能发汗,多服之则洒洒汗出不止,是以不敢用焉。此是何言也,譬怯者之于妖怪,足不尝踏其境,而言某地真出妖怪也。为则尝试麻黄之效,可用之证而用之,汗则出焉,虽当夏月,而无洒洒不止之患。 仲景言服麻黄后覆取微似汗,宜哉,学者勿以耳食而饱矣。麻黄本身发汗之力诚亦平常,如得佐药,而其功乃著。如恶寒、无汗、发热之证,恶寒多佐以桂枝,发热甚佐以葛根,又恶风寒、关节痛颇甚,可以配附子,若与石膏同用则灵妙更不可名状。近世医工一见表寒行将化热,喘渴并见,虽知必用麻黄解表,而顾忌其辛温,于是连翘、桑菊、大豆黄卷、冬瓜子,摇笔即来,所谓辛凉清解,或凉解表邪者,轻者尚效,重者必传阳明无疑。吾以为若以麻黄、石膏并进,麻黄解其郁热,石膏平其烦渴,麻黄之辛温得石膏之甘寒调剂之,更何不可用之有? 东国喜多村曰:“石膏与麻黄同用,则有走表驱热以发郁阳之功。”“以发郁阳”四字,盖深得仲景方义者。又麻黄与石膏同用,有时可作强心剂用之,盖钙能增加心脏之紧张力,麻黄能亢进血压之故也。麻黄除发汗外,定喘亦为主要功用,近世陈克恢博士从麻黄中提出有效成分爱非特林(亦名麻黄素),主要功用亦为气管支喘息之妙药。按气管支喘息之原因虽有种种,然不论其原因如何,主症总不外乎气管支之痉挛,爱非特林能使痉挛之气管支弛缓,气管支弛缓之后则腔径开大,而后气喘自平。吾友张伯瑜医师,述近日德意志医界,不特常用麻黄之治气管支喘息,并有人能用华方者,其师医院时,即有手订治疗气喘之华方,且将药品储诸西式药瓶,以备不时之用。就中麻黄,并知恪遵古法,先煎去沫,亦趣闻也。方如下:麻黄先煎去沫八分,白果三粒去壳打碎,炒苏子钱半,炙款冬钱半,姜夏钱半,杏仁钱半,制川厚朴一钱,炙紫菀钱半,甘草八分。 准如上述,麻黄之定喘,其适应证为气管支喘息……麻黄用于气管支喘息所以奏效之理,即因爱非特林用于气管支痉挛时,由交感神经末梢之刺激,血管得以收缩,而急性之黏膜肿胀得以减退,爱非特林有麻醉作用,更能麻痹气管、筋肉,故已痉挛之气管支、筋肉得以弛缓,于是气喘平。 小儿之顿咳,俗名虾蟆咳,即西籍所谓百日咳,始则黏膜发炎,终则入于痉挛期,有特异性痉挛性咳嗽发作。古方治此病,亦有用麻黄者,如鸬鹚涎丸。古人谓本病因于风寒伏肺,麻黄能宣利肺气,故治之。实则麻黄之治此病,亦不外弛缓痉挛而已。或曰:麻黄之用在弛缓气管痉挛,谨闻命矣,小儿痧子后每见气急鼻扇,麻杏石甘汤是要方,则小儿痧子后气急鼻扇,亦属之气管痉挛乎?答曰:非是,小儿痧子后气急鼻扇是卡他性肺炎现象,凡肺炎以呼吸困难为特征,呼吸之所以困难,乃因肺循环每多郁血,因肺之呼吸面积为之缩小,故鼻乃从而扇动,西医恒用强心剂疗治,使肺循环郁血减退,则肺炎自能缓解,而呼吸困难亦能畅顺。麻黄有亢进血压之效,能祛除血行障碍,其作用与毛地黄阿特列那林同,故应用于肺炎,亦能消除肺郁血,减退肺之炎症,呼吸因之畅利,且因能亢进血压之故,肺炎时随发之心脏衰弱亦得以恢复。大论:汗出而喘,无大热者,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。 近贤恽铁樵氏《伤寒辑义》按,以为麻杏石甘总非有汗之病可服,本条经文似当作无汗而喘,大热者,则无疑义矣。按恽氏此说可商,自汗出身无大热之喘息,吾人平日临证,不时遇之,审为肺循环郁血,或气管支喘息,总以麻黄为主药,而以他药副之,病无不愈。宗人太炎先生论肺炎之治,咳嗽发热,喘息不甚者,无汗宜小青龙加石膏汤,有汗宜麻杏石甘汤,何尝以有汗而禁绝麻黄不用。故凡以有汗、无汗定麻黄去取,殊不尽麻黄之用,其失盖与恽氏同矣。麻黄又可以应用于肺气肿,肺气肿者,非原发病,多由慢性气管支炎续发,咯出之痰为白沫,多气泡,呼吸困难,往往不能平卧,国医浑称为痰喘,或痰饮,或咳逆,麻黄有强心作用,故用之有效。周身浮肿所起之呼吸困难,国医名曰喘肿,盖浮肿时胸腔积有水分,压迫肺脏,致发生呼吸困难,此时用麻黄亦有效,因麻黄具有利尿作用,小溲通畅而浮肿减退,肺部无所压迫,则呼吸困难自除矣。例如受孕至末期,孕妇恒多呼吸困难症状,此亦因腹部膨胀,子宫腔上升,肺部受其上升之压迫,而发生呼吸困难,一俟分娩,呼吸即平,其理一致也。(《章次公论外感病》) 李健颐经验麻黄医话 李健颐(~年)李健颐,原名孝仁,号梦仙。祖籍晋江县池店乡。健颐之父精于医术。他从小受其启蒙,勤读中医书籍,随父诊病。后又毕业于上海中医学校,奠定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。年,他参加组建福建省中医学院及中医研究所。历任省中医学院院务委员、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、省中医学院温病教研组主任、医院内科、肿瘤科主任、《福建省中医药杂志》编辑室主任等职。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第一批确认为名老中医。专著有《黄帝内经知要浅注》、《四诊概要》、《汉药便览》、《临症医案笔记》、《病例论文汇集》等10多部。 痨病误服麻黄斗垣村,林生,患痨病,咳嗽,哮喘,痰涎壅甚,胸胁微痛,口燥咽干,初服补肺化痰药稍愈,嗣因读书劳神,症急变重,略有动作,喘促愈甚,延某医诊视,云系肺脏伏热,投麻杏甘石汤,初服1剂喘气见平,痰涎亦少,意为药已中肯,遂连服10余剂,病热反重,哮喘面黑,唇反口开,大汗溱溱,气促不卧,食欲不振,改延于李氏,曰此病肺胃俱败,血脱气奔,二竖相侵,恐难为力。阅前方麻杏石甘汤,每剂麻黄6g,据云初服甚效,遂连服10余剂,今因何故反变危笃?李氏曰此症之害,由于多服麻黄之故。麻黄辛温发散,性最烈,善发汗,且能夺血。仲景云:夺血无汗,汗即血液,过汗则伤血,血伤则脏腑无营养之能,血液无涵润之功,死血凝滞皮间故现黑色。《洗冤录》云:病人服麻黄过度,肌肉转变黑色。由此可知林生是由发汗夺血,血败气散,可无疑义矣。林生闻言,才觉是误,忏悔不已,其症日重,延至月余乃逝。 细思其病,初非死症,由以多服麻黄,耗伤精血,竟至于死,其可悲也。夫麻黄能鼓散肺中伏寒,发出于肌腠之外,由汗而解,兼治太阳伤寒病,如确系麻黄证,已服过麻黄汤,见有汗出,尚不宜再投麻黄汤,恐重汗伤营,变病蜂起,况肺痨症之与麻黄相反者乎。《伤寒论》云:“尺中迟者,不可发汗,以营不足血少故也。”此仲景所以戒人发汗伤阴之意,今林生不知麻黄是肺痨之劲敌,肆意服用,竟至误害,诚可惜哉! 阳水重用麻黄得奇效病者王某,年52岁,住福建福清县后山顶村。病者患水肿有1月余,开始四肢及面部浮肿,延至全身肿满,肿势甚剧,连衣服都不能穿,兼有发热无汗、咳嗽气喘、呼吸困难、大便秘结、小便短赤等症状。即断为阳水实证,用越婢汤加减治疗。方用麻黄30g,石膏60g,甘草4.5g,车前子30g,白茅根60g,生大黄15g。取麻黄有开肺经发汗的作用;石膏泻阳明经之热,并有监制麻黄发汗过猛的作用,为发汗退肿之君药,就是“开鬼门”之法;佐车前子、白茅根,泻膀胱、三焦二经之蓄水,为利水治炎的臣药,就是“洁净府”之法;加大黄荡逐大肠之积水,俾从大便排出,即“去苑陈莝”的意思,也是一种急则治标之法。此方服半剂,至夜半2时许,连下小便4次,腹胀顿消,浮肿也退。次日复诊,依原方减为半剂量,再服2剂后,霍然而愈。继以葡萄糖、维生素调养半个月而收功。 此方的用意是依《内经》所说三焦属肾,肾上连肺,故肾将两脏,三焦者中渎之府,属膀胱及肺与大肠表里等的意思。就是说明肾、三焦、膀胱、肺、大肠的各部经络都是有相互连络的关系,是取其连络的关系意义为治疗的法则。(李健颐整理)(《临症医案笔记》) 叶熙春经验论麻黄 叶熙春,男,(—),名其蓁,字熙春,籍贯,浙江慈溪,从良渚名中医莫尚古习医,研考医学典籍,深得其旨。年,至上海行医,接连治愈若干疑难绝症,名声益振,江、浙、皖诸省慕名求医者亦众。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,并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。于年10月含冤而逝。年8月平反昭雪,恢复名誉。年,省卫生厅整理总结他的临床经验,编印出版《叶熙春医案》。年,又汇编出版《叶熙春学术经验专辑》。 一日,先生治一痰热咳喘证,处方以麻杏石甘合葶苈大枣二方加味。诊毕,环顾侍诊学生曰:本草以麻黄为发汗要药,又曰麻黄发汗,麻黄之根、节止汗。读仲景书,以麻黄汤为发汗要方,治发热、恶寒、无汗、脉浮紧之太阳伤寒。但该方去桂枝则名三拗汤,专治外感风寒之咳嗽气急,由此可见麻黄与桂枝或紫苏叶、生姜辈为伍,其功在发汗解表、宣散风寒,若无此类药物相佐,则发汗力弱,长于宣肺涤痰、止咳平喘。再如阳和汤治阴疽,方中也用麻黄,意在领诸药外出肌腠而建功,也非发汗之需也。 麻黄者,生用力峻,蜜炙力缓,量多力竣,量少力缓,合桂枝或紫苏叶、生姜等发汗力峻,不合此类辛温发表药则主要用于祛痰平喘。临床应用时须按治疗需要把握剂量,若用量在1.5g以内,麻黄亦可止汗,其效果与麻黄根、麻黄节相近。(李学铭等整理)(《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?叶熙春》) 耿鉴庭经验麻黄治喉 耿鉴庭(~)著名耳鼻喉科专家、医史学家、文献学家。年10月15日生于江苏扬州六代中医世家。其父耿蕉麓为扬州著名儒医,名噪大江南北,犹以医德望重乡梓,所居里巷,名之为"耿家巷"。先生幼承家学,十四岁即完成儒学经典教育,后专习医学,遍读医宗经典并随父应诊,打下坚实的中医理论功底。18岁开始独立应诊。20岁复入江苏省立医政学院(今南京医科大学)学习,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,成为中西医兼通的医生。耿鉴庭先生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,国家科委预防医学组常务委员,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,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副主任委员,《中华医史杂志》副总编辑,全国中医中心图书馆副馆长,中医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,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,学位委员会委员,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,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,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,国务院古饵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,《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》名誉总编辑,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会员,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会员,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,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。年第一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 姜步庭先生用麻黄以治暴感风寒之失音。耿家用以治喉,暴感风寒,咽喉痛而咳嗽气喘、声音变化者,多伍射干、杏仁等用之;感受风热,咽痛气粗者,多伍杏仁、石膏等用之;伏湿感风,咽门水肿者,多伍杏仁、薏苡仁、甘草等用之。麻黄又为治喉外用药。《圣惠方》治语声不出,麻黄以青布裹之,烧烟筒中熏之。耿氏曾试用于声门水肿者,果有良效。用量为4g。 麻黄煎汤,上有白沫,陶弘景谓“沫令人烦”,确是事实,故以去之为宜。(耿刘同、耿引循、刘慕伦整理)(《喉科正宗》) 李翰卿经验麻黄应用体会 李翰卿(~)医学家。字华轩,又名希缙。大同市灵丘县沙坡村人。舅父张玉玺乃当地有名的儒医,李氏自幼从其学医习文,日积月累,加之勤奋刻苦,终于尽得其传。李氏15岁时即能治疗一般的疾病,以后虽在当地小学任教,但每有闲暇即为人疗疾,以治病救人为乐,逐渐医名日增,求治者盈门。27岁时,由本县推荐到山西省立医学传习所(川至医专前身)应试,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。经过3年的寒窗苦读,他不但系统钻研了中医经典,对历代各家各派学说亦多有涉猎。年毕业,先后应邀在太原复成堂、体乾堂等行医。35岁始独立开业,悬壶并州。由于其医术高超,就医者络绎不绝,渐次在省城声名大噪。李氏因其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,被誉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,并深受中医界同仁爱戴,被公推为太原国医公会执行委员。年进行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的研究,获得成功,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之一。年编著《伤寒论方临床使用经验》。 麻黄发汗解表,医家言其为诸药之首,然其用于临床亦有不见发汗者,亦有少量用之而大汗不止者,综其原因有三:一是新鲜者发汗作用强,陈久者发汗作用弱,甚或无发汗作用;二是气虚、阴虚证发汗作用强,风寒闭郁至甚者发汗作用弱;三是热证发汗作用强。 麻黄宣肺定喘,医家言其为诸药之首,然其用于临床有有效者,有加剧者,综其原因有二:一是风寒闭郁、肺气不宣之咳喘其效甚佳;二是肾不纳气之喘和肺气虚的喘用之必甚。曾治一咳喘难止之患者,先予诸种定喘止咳方无效,后邀余治,诊为肾不纳气,予金匮肾气加蛤蚧,某医恐其无功酌加麻黄无效,及至改为去麻黄后愈。(朱进忠整理)(《山西名老中医经验汇编》) 陈苏生经验麻黄与麻黄根同用之探索 陈苏生,男,汉族,江苏省武进人,生于年,年1月去世。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,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,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。先生16岁时,经介绍至上海名幼科沈仲芳之门,从师3年,后又拜钟符卿先生为师。年拜识了祝味菊先生,经几度长谈,心悦诚服地列于祝氏门下。先生经常向祝师质疑问难,探求医学之真谛,后将所录笔记仿《内经》问难的体裁,辑成《伤寒质难》一书,首创“五段八纲”学说。年被调往中国中医研究院进行筹建工作。年医院。先生返沪后,医院、市第一结核病院中医顾问。年经人事部、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,确认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年被评为“上海市名中医”。 麻黄全草都有药用价值,地上茎部的绿色茎柱名曰麻黄,亦名青麻黄;地下根部的紫色根节曰麻黄根。实验证实,茎、根两部的麻黄具有相反的生理作用。麻黄能升高血压,麻黄根则可使血压下降。麻黄具有发汗作用,而麻黄根则止汗甚捷;麻黄有兴奋避倦之能,麻黄根则有镇静摄纳之效。在传统处方中,麻黄与麻黄根从来就是区别分开,从无麻黄与麻黄根并列使用之先例。年陈苏生老中医在中西医结合病房中,收治各种慢性呼吸系统病变的重症患者,其临床表现以咳嗽痰多、喘息、胸痞等症状为主,或苦于反复感冒,或困于长期失眠。治疗喘咳西医曾选用麻黄来排痰定喘,由于麻黄有兴奋之弊,不利于高血压失眠患者,有时加用西药镇静药,但效果不理想。陈老创议用相反作用之麻黄根与麻黄同用,以此来纠正麻黄之不良反应,使其更好地发挥麻黄之定喘排痰作用,效果非常满意。于是逐步推广应用,咳不爽、痰不利、气逆不顺、上逆作喘等患者亦收到相应效果。陈苏生老中医创立了二麻四仁汤方:麻黄4.5g,麻黄根4.5g,桃仁9g,苦杏仁9g,白果仁9g,郁李仁9g,蒸百部9g,款冬花9g,车前草24g,甘草4.5g。方意:二麻同用,一开一合,宣畅肺气,以排除通气障碍。桃仁、杏仁,二味同用,一气一血,桃仁消散肺部瘀血,杏仁降气化痰,两者具有润肺镇咳之功。白果定喘,能收敛分泌过多之痰,郁李仁滑痰利水,以润导大肠之燥结。二味同用,一滑一润,使已成之痰能化,未成之饮能敛。百部、款冬花,一名百花膏,治暴嗽久嗽。车前草既能镇咳,又能排痰。甘草同用为已故名医余云岫之秘方(小儿咳嗽糖浆),与百花膏同用,有宁嗽和肺之用,无硬性镇抑之弊。各种病菌引起哮喘最易感冒,如新有感冒,则加入土茯苓30g,忍冬藤15g,连翘10g,白薇10g,对消炎抗菌有积极作用。如见消化障碍,则加入柴胡9g,生牡蛎30g,苍术9g,川厚朴9g,以宣和气血,平胃宽中,因病而有出入。(陈苏生整理)(《上海地区名老中医临床特色经验集1》) 陈老认为,见咳止咳,而咳不止者,必去其致咳之因。古人有“咳无止法”之戒,又有“肺如悬钟,不叩不鸣;外感之邪,叩之则鸣;痰浊内壅,上逆于肺亦鸣”之说。治疗对策,当以开肺排痰为先。他常常教导我们:肺有上口,而无下口,痰蓄积于气道,随喘息呼吸上下,则成痰鸣,保持呼吸通畅,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成败的关键。 二麻四仁汤,以宣畅肺气、排除痰浊、强心利尿为中心,对哮喘、慢支、肺心等顽疾,因痰多积液壅滞而致咳不爽、痰不利、气逆不顺、上逆作喘等患者,大都能收到相应的效果。方中麻黄辛散开腠理,宣肺气,解痉定喘,乃发散肺部邪郁之良药。麻黄根固表止汗,能制约麻黄之副作用,不使肺气开泄太过。二麻同用,一开一合,一兴奋,一镇静,一扩张血管,一收缩血管。因此,二麻同用,既可增强肺活量,以利其通气功能;又可宣开肺部之郁血,而不致伤其肺络。一张一弛,从而收到增强肺功能、排除通气障碍的作用,又无升提血压、助长兴奋之流弊。杏仁走气分,降肺气之上逆;桃仁走血分,化血络之凝瘀。二者合用,一气一血,既能顺气降逆,涤痰解凝,又能流通肺部郁血,古今医家,咸同此理解。郁李仁行水道,通大便,有通下定喘之效,近人有用以为主治药者。白果仁敛肺不敛痰,能抑制痰浊的过度分泌,长于稀释凝痰。二者合用,一滑一涩,使已成之痰能化,未成之饮能敛,与仲景治喘有姜、辛、味三味合用之法,含量相似。百部、款冬花合用,乃《济生方》之百花膏,擅治暴嗽、久嗽。车前草既能镇咳,又能排痰,与甘草同用,加强了宁嗽和肺之用,而无硬性镇抑之弊。 二麻同用,在上千病例中无发生血压升高、影响睡眠等流弊;相反由于肺气畅达,排痰滑利,而取得种种有利之机转,说明麻黄与麻黄根是可以同用的。陈老常说:“师古而不泥古,临床加减,皆是活人活法,毫无拘泥,方能奏效。”看来是有很深刻道理的。 二麻四仁汤是陈老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独到经验良方,此方虽祛邪,实为扶正。陈老的学生们以此付诸临床实践,凡是咳嗽、胸闷痰多、气逆诸症,只要同样具有通气障碍的病理机制,纵使病种不同,皆能收到同样临床的疗效。其临床加减法:有热象者,加土茯苓、忍冬藤、连翘、白薇;兼肾虚者,加枸杞子、补骨脂、胡桃肉、磁石、冬虫夏草等;肺阴不足者,加沙参、麦冬、知母等;胸阳不振者,加桂枝、白芍、细辛、生姜等。 病案举例:顾某,女,50岁。有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史20余年,且病情逐年加重,每年有2/3时间发病,1/4时间卧床。近几年来,唯靠静注氨茶碱、地塞米松、先锋霉素等药度日,肺活量仅为常人之54%。曾用多种药物及不同疗法治疗,皆无显效。来诊时步履艰难,动则气喘,头脑胀痛,食欲不振,心悸梦多,形神萎顿。舌苔薄腻,脉沉细。病久正气日亏,不可蛮补,且痰浊内凝,须缓缓调之,非旦夕能收功者。乃用二麻四仁汤随症加减治之,药至剂,病情逐步得到缓解,痰浊去,喘息平,食欲馨,夜寐甜,哮喘也由大发至小发,终至不发,且行动自如,生活已能自理,西药也逐渐减量,乃至停用。随访5年,疗效稳定。(陈明华整理)[浙江中医杂志,(3):99] 刘渡舟经验麻黄治喘,寒热咸宜 刘渡舟(年10月9日-年2月3日),原名刘荣先,年10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。幼年时,因体弱多病,常年请中医大夫治疗,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疗效,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。由于他体质虚弱的原因,他的父亲在择业时给他选择了中医这条道路。16岁时在营口正式拜当地名医王志远先生为师,矢志学习中医,从而迈出了此后漫长中医生涯的第一步。着力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。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,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。提出《伤寒论》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临床辨证善抓主证,并擅长用经方治病。著作丰富,校定原文,其《伤寒论校注》被认为当代最具权威性的校注本。顺文解释,如《伤寒论诠解》。归类编注,如以证分类之《伤寒挈要》,以方类证之《新编伤寒论类方》。专题发挥,如《伤寒论十四讲》、《伤寒论临证指要》。普及读本,如《伤寒论通俗讲话》、《医宗金鉴.伤寒心法要诀白话解》。编撰教材,如《伤寒论选读》、《伤寒论讲义》。主编辞书,如《伤寒论辞典》。 麻黄治喘,寒热咸宜,与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相配则治寒喘;与石膏、桑白皮配伍则治热喘;与杏仁、薏苡仁相配则治湿喘。除心、肾之虚喘必须禁用外,余则无往而不利也。(陈明等整理)(《刘渡舟临证验案精选》) 姜春华经验哮喘汗出不忌麻黄 姜春华(~年),字秋实,汉族,江苏南通县人,全国著名中医学家、中医脏象及治则现代科学奠基人。先生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,18岁到沪悬壶,复从陆渊雷先生游,30年代即蜚声医林。年先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任中医教研室主任、脏象研究室主任,相继兼任内科学院(医院)、医院中医科主任。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、上海分会名誉理事长,先后被聘为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、上海市中医学院、上海中医药研究院、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。 江南过去某些医师倡言“南方不比北方,夏月不可用麻黄”,于是夏天哮喘发作当用麻黄而不用。又有些人说“仲景明训”,“有汗用桂枝,无汗用麻黄”,认为凡汗出者均忌用麻黄,于是哮喘发作时汗出者又不用麻黄。临床上很多患者在哮喘大发作时常大汗出,如果喘平下来则汗亦少出,当以平喘为主,不平喘则汗不得止,为了有汗避开麻黄,则喘不得止,汗亦不得止。前人有鉴及此者,如王旭高麻杏石甘汤注:“喘病肺气内闭者,往往反自汗出。”“用麻黄是开达肺气,不是发汗之谓。”“且病喘者虽服麻黄而不作汗,古有明训,则麻黄乃治喘之要药,寒则佐桂枝以温之,热则加石膏以清之,正不必执有汗无汗也。”诚有识之见。可以推论,凡对某病证有良好作用的药物,不必因有某种不良反应而避开不用,也不必受非主要症状的牵制而不敢用。当然用量应斟酌,中病即止。(俞栩整理)(《名老中医医话》) 哮喘病的治疗,自古以来多沿用《伤寒论》以麻黄为主药的方子。如麻黄汤、小青龙汤、大青龙汤、越婢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等,依病者的寒热虚实辨证而用。晋唐验方也都以麻黄为主,但用至30~60g者,疗效仍不理想。中药的有效量和极量至今仍未确定。过去医生们用麻黄只用0.3~1.5g也有作用,同30~50g相比,用量相差悬殊。姜氏平日习惯用6~9g,不过多也不过少。在农村用二拗(麻黄、甘草)、三拗(麻黄、杏仁、甘草)于儿童,用麻黄汤于成人,效果良好,乡人用药易见效,城市则不然。麻黄平喘之功不可没。(姜光华整理)(《古今名医临证金鉴?咳喘肺胀卷》) 胡天雄经验哮喘汗出不忌麻黄 胡天雄,男,汉族,年生,湖南省双峰人。湖南中医学院教授。早年随父在农村行医,并学习中医内、外科。年湖南中医学院,医院内科、肿瘤科医师,后调内经教研室任教,年负责主编《湖南中医学院学报》至年退休。临床强调八纲应万病,万病不离八纲的辨证原则。认为时无分古今,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老幼,病无分急性慢性、传染与不传染,患者的具体症状,无不有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之可分。著作有《素问补识》、《诊余漫记》、《马王堆医术考注》等。 《伤寒论》63条:“汗出而喘,无大热者,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。”汗出而用麻黄,无大热而用石膏,与常法不合,胡氏年轻时读此条,甚感疑惑不解。后于戊子夏初,遇一李姓妇女,哮喘大发,胸闷自汗,气憋难耐。胡氏见其汗臭熏人,试予此方,使麻黄与石膏同用,一服症状即平。因知凡事实所有而理论不通者,当舍理论而从事实,因事实可以验证而理论有待探索也。柯韵伯妄改此条为“无汗而喘,大热者”则削足适履之见,不足取也。本方“汗出而喘”与葛根苓连汤之“喘而汗出”,前者重在喘,后者重在汗出,仲景画龙点睛,往往点在“而”字后面,太阳伤寒之“而恶寒”,太阳温病之“而渴不恶寒”,小青龙证之“而咳”,大青龙证之“而烦”,悉循此例,姜佐景氏已先言之。虽然此“汗出而喘”条置在《太阳篇》中,乃指阳证实证而言,若真阳暴脱,气息坌涌,魄汗未藏,四逆而起,则少阴危症毕露,医护不得离床,黑锡、姜、附所当急进者,与麻、膏之喘汗,又有毫厘千里之别矣。(胡静娟整理)(《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——胡天雄》) 名医经验整理小组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jintiesuos.com/sbpjg/183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31名国宝级名老中医秘方集锦
- 下一篇文章: 邱老临证医案实录28慢性喘息性支气